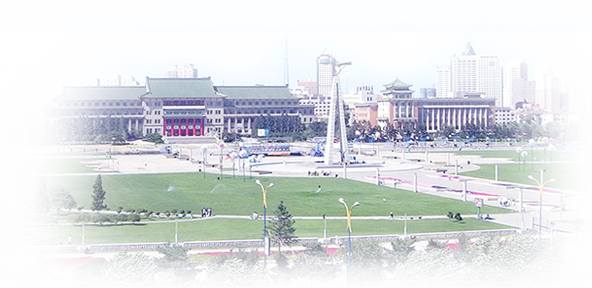随着首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制度效能论”的提出,民主党派及其所依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再一次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作为党内法规,虽然《条例》在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实施方式,包括对外发布方式上均有一定限制,致使社会反响良好之余,略有“养在深闺”之憾,但较之以往,首部关于党的统战工作全面规定的出台,使统战工作从此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参政党建设走向法治化的重大进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留下的这笔宝贵的政治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局中、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中能否展现出它理想中的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能否准确地认识民主党派的定性与定位问题。
解读中国的民主党派,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二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三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一、特色道路上的特色政党
(一)从政党的基本属性看,民主党派是新型政党
在中国政党制度确立之前,关于“政党”的概念是由西方政治理论来界定和诠释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政党的定义是:“政治体制内为取得和行使权力的目的而组织的集团”;《日本大百科辞典》认为:“政党是以取得国家权力为目标而基于共同的政策组织和动员国民、开展一切政治活动的持久性的政治团体”;在中国的传统教科书中:“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这意味着在政党认识上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即谋取政权是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政党存在的基本要义。
参政党概念的提出,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定式,丰富了世界政党理论和政党政治理论的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史上实现了两个创新:政党概念的创新和执政形式的创新。它创制了新的政党类型,拓展和深化了对政党基本属性的认识:政党可以放弃执政资格,参政也是政党的政治参与方式;它创制了新的合作政党体系,拓展和深化了对政党关系性质的认识: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只是政党体系的内部分工,有效地解决了政治资源浪费问题。
(二)历史起点决定道路逻辑
“吾国古无所谓政党也,披览史乘,只有朋党之可稽。”直至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传统帝国体系在民主政治的诉求中轰然倒塌。1905年,中国最早的政党——中国同盟会诞生,此后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政坛上出现了大大小小300多个政党。到20世纪40 年代,中国社会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并存的格局:国民党、共产党和以“三党三派”的集合体——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各党各派由于自身利益不同,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
在20世纪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是绝对的主角,各派政治力量只能在国共两大政党的政治分野中,做出自己的抉择。青年党和社会党投向国民党,至今在中国的政治图谱中已经了无痕迹;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怀揣理想抱负和道德良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洗礼,在实践中,得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从此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不同于英国民主起源于有产者权利保护之斗争,不同于法国民主发轫于下层阶级争取自由之革命,也不同于美国民主肇始于特殊历史机缘和地理条件下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双重开放,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于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中,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调动最广大的人民抵抗外侮、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政治机制。从统一战线的理论维度看,它必须解决好同盟军问题、领导权问题和战略策略问题。历史起点和历史主题的输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道路,也使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烙上了鲜明的特色:即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中共的主体性、党际关系的合作性,以及在战略和策略上的长期性。
二、特色政治文化中的特殊角色
(一)从政党的角色定位看,民主党派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构成的政党
民主党派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是以温和的改良派政党出现,其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他们是民族抗战的重要宣传者,是战时民主的重要追求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保护者;他们引导着当时的社会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并夺得政权,与此不无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工农没有知识分子帮助,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党、治国、治军。”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的代表性人士为核心,以个人的声望和魅力去影响追随者、发展组织,成为民主党派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因此,考量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
(二)文化基因与政治传统
在中国,“政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中就有“掌其政治禁令”之说。“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文明的最初形态决定了其对中央权威的依赖程度。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则是社会政治结构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不断地强化初始条件,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大屋顶”的政治架构和集权专制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主宰着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政治史,也制约着百年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首先,2000余年的大一统国家历史,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大国治理经验,发展出一整套治理大国的“士人政治”传统,相对于西方而言,长期延续了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存了文明的源流。“士人政治”传统最大的优势,是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统一。执政集团以儒家“民本主义”为指导原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在政治责任感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远大于西方阶级政党意义上的政治“代表性”的特征。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而从传统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一党执政延续着“士人政治”的历史惯性。因此,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执政者同时被视为国家的保卫者和中华文明的守护者,这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其次,这一传统也造就了中国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只不过开放的表现形式不同。如果说西方政治的开放性是通过议会民主、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外部多元化”来实现的,中国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则表现为“内部多元主义”,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是“皇权”与“治权”的分离,体现在政治文化上,是“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张力结构。
(三)知识分子与士的精神
知识分子是现代概念,起源于西方。仅就其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一基本性格和特殊涵义而言,知识分子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称为“知识分子”之前,叫做“士”。士的精神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独特的品性和特征:
首先,士志于道。以“道”自任,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强烈和最本质的特征。“道”的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由来已久,且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发展的始终。但中国人的“道”既不寄身于宗教,也不托庇于思辨形而上学。“道”超越现实的世界,却不脱离人间,换言之,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士的天职和使命就是守道、卫道、传道,他们对“人间世”的关注,主要就是用一种超越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
“士志于道”的价值追求促进了知识分子参政的自觉性和根深蒂固的“入世(仕)情结”,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从孔子开始就不仅是“坐而言”的理想主义者,更是“起而行”的道德实践者。正如余英时所说:“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在朝为士大夫,凭借政治力量造福天下;在野为士君子,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绵延不断,至今犹存,确是世界文化史上最独特、最光辉的一页。
其次,从道不从君。孔子以前是道政合一的圣王政治形态,其后“道统”与“政统”一分为二。“道统”以“内圣”为核心,“政统”以“外王”为本质;“道统”执着在护持德行修养的“自律”,“政统”倾向于维护政治秩序的“他律”;“道统”走的是“内在超越”之途,“政统”行的是“外在规范”之路。
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既寻求理论的统合,试图以“圣”制约“王”,又在政治理想及其理想人格与君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形成了以道抗政、以德抗位的传统,以限制皇权的过度集中专断。中国传统政治就是一部君权与官僚制度不断相互摩擦、不断调节的历史。不理解“道”与“政”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理解“风骨”和“反骨”的本质区别。
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品性,塑造了中国民主党派独特的气质和灵魂,也使中国的政党拥有了迥然于西方政党的独特的文化解释,尽管双方都使用“政党”的概念。
三、特色国情下的特定责任
(一)从政党的政治属性看,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政党在中国兴起,从观念上,本是西方政治思潮流布和实践之结果。各民主党派形成时期的时代特点、阶级基础及其主要成员的政治倾向,决定了其政治纲领的基本精神: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政治民主。前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后者则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党派是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民主党派比较接近西方政党,在主张上也比较倡导西方模式: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制、内阁制,经济上确保私有制,建立“新式”、“改良”资本主义,思想上是自由主义,行动上是和平改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民主。
建国后,中共对民主党派性质的界定历经变迁和曲折:从“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过渡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政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到“资产阶级政党”,几经反复;直到文革结束,方逐步发展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及至“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参政党直接联结起来,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属性,解决了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姓“社”的根本问题。
中国政党制度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跳出政权兴亡历史周期率”,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逻辑而构建的一种制度设计。人民民主专政从根本上规定了它的核心价值和制度要素:民主党派不是与共产党分庭抗衡的反对党,不是与共产党分掌政权的联合执政党,而是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参政党;“跳出政权兴亡历史周期率”从功能上规定了它的设计初衷: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不是分权制衡关系,而是体系内的权力制约关系,其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反对或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与西方多党制和前苏联一党制的政治模式彻底分道扬镳。
民主党派存在的价值,从政治架构上看,列入了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从政治功能上看,“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从民主价值上看,民主党派以民主为价值取向,与中共有共同旨归,作为参政党托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呈现。它拓展和深化了对民主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民主的内涵是丰富的,民主的形式是多元的。谋求共识是民主的灵魂,合作与协商理应成为更好的民主表现形式。
(二)参政党的首要责任是政治责任
政党是政治组织。政党产生至今,始终与民主政治进程交织在一起,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工具。政党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哪种政治制度,各类政党的首要责任就是政治责任。实现政治功能是民主党派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有两个基本意涵:其一,意味着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意味着民主党派不在政治生活中谋取执政权力;其二,这并不表示民主党派放弃政治追求,从而导致其政党政治功能的丧失。参政党的政治功能和民主价值能否得到多元化立体化的全方位演绎,是透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风向标。
但政治这一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或者同一制度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与胡耀邦讨论“什么是政治”,他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2014年12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两段话可谓一针见血,是对各自所处不同历史阶段关于“政治”的最精彩的概括。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举旗定向、勾画蓝图,是对中国未来的宏观布局;四中全会构建了中国的法治大厦,绘就了法治中国的路线图。但改革要破局,法治要推进,文化要传承,民族要复兴,不仅需要执政者的智慧、勇气和铁腕,更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和支持。在这场“人心向背”的攻坚战中,民主党派不仅要讲政治,还得干政治,还得干好政治。讲政治讲的是立场和方向;干政治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价值;干好政治是要把握尺度,准确定位。费孝通说:“民盟的责任就是要协助共产党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具体而言,在当今中国,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就是参政党最大的政治。
回顾百年中国,有人对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到新中国成立,我们依靠军事力量解决了“挨打”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依靠经济力量解决了“挨饿”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挨骂”问题,换言之,亟需构建一套自成一体的价值体系,以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要解决这个问题,“继续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主要依靠的是“思想的力量”,这是知识分子的优势。
中共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智库”的概念,今年1月,中央两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共大兴智库,事实上是开启了思想市场,除了通常所讲的譬如科学决策的需要,重要原因在于,在意识形态工作被提到“极端重要”的高度的今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希望通过开启思想市场为中国思想理论建设寻求新的突破口,升级理论武装。填补理论空白,推进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政治坐标和话语体系,既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构成的民主党派政党份量和存在价值的具体体现,更是举好旗、走好路的方向问题。
知识分子的价值乃在于认识世界,为执政者改造世界提供相匹配的理论支撑和文化涵养。在这条前无古人的特色之路上,参政党当以君子之德行、渊博之智识、专业之素养、学以致用之能力,不缺位、不越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支撑起一片思想和文化的天空。
来源:协商新报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